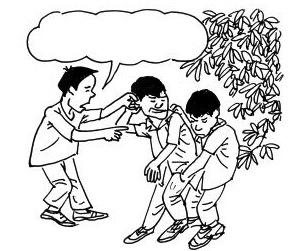
陈洪兵
【摘要】“抢劫致人重伤、死亡”中的死伤,应限于与抢劫行为具有密切关联性、按照社会一般观念通常伴随发生的死伤结果;抢劫故意杀人的,成立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想象竞合犯,通常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尤其是抢劫故意杀人而未发生死亡结果时,应以故意杀人罪的未遂论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而未取得财物,以及具有重伤、杀人的故意而未发生重伤、死亡结果时,成立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未遂,适用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法定刑,同时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未遂犯的规定;抢劫致人死亡而未取得财物的,成立抢劫致人死亡的未遂与故意伤害致死的想象竞合犯;只要抢劫共犯人对于死伤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一般难逃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刑责;根据因果共犯论,抢劫共犯仅对与自己的参与行为具有因果性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不对参与之前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共犯责任。
【关键词】抢劫致人重伤、死亡;成立范围;抢劫故意杀人;既未遂;共犯
【全文】
刑法第263条抢劫罪规定,“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2001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抢劫杀人批复》)指出,“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按照该批复的精神,在抢劫过程中意图杀人而向被害人要害部位连捅数刀后逃离,后经鉴定仅构成轻伤或者轻微伤的,只能以抢劫罪(而不是故意杀人未遂)定罪,适用抢劫罪的基本刑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这种处理结论可能导致罪刑失衡。此外,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抢解释》)第十条指出,“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八种处罚情节中除‘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这一结果加重情节之外,其余七种处罚情节同样存在既遂、未遂问题……”。言外之意是,“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只有成立与不成立的问题,而没有既未遂的问题。殊不知,虽然刑法分则规定的情节(结果)加重犯中属于量刑规则的不存在未遂犯,但“抢劫致人重伤、死亡”作为加重的犯罪构成,当然存在未遂犯。[1]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刑法理论会认为,抢劫致死伤罪无未遂。
司法解释一向被实务部门的同志奉为圣经。诚如杨兴培教授所言:“司法实践中好像没有了司法解释,我们的法官们就会寸步难行。司法解释俨然替代了刑法典本身而成了法官裁判定案的主要依据,长期以往,法官们将大有不知刑法典为何物、有何用处之普遍现象。在这种司法解释牵引下的司法实践恐怕再也没有仰望法律、进行精神信仰的思考和面对问题进行全力索解的努力。”[2]司法解释不过是一种“解释”而已,并非法律。一方面,司法解释不可能给出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若没有司法解释,或许还有个别地方、个别法官办“对”案件,倘若司法解释本身就是“歪嘴和尚念经”,则几乎不会有法官办“对”案件的可能。抢劫致人死伤的相关问题,一向是国外刑法分则解释论中的“宠儿”,也是司法适用中的难点。准确解读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成立范围
抢劫罪,作为暴力性财产犯,其行为本身往往具有致人死伤的高度危险性,因而各国刑法都有抢劫致人死伤的相关规定。例如,德国刑法第251条抢劫致死罪规定:“如果行为人由其抢劫至少轻率地造成他人的死亡的,那么,处终身自由刑或者不低于十年的自由刑。”日本刑法第240条抢劫(原文为“强盗”)致死伤罪规定:“抢劫致人负伤的,处无期或者六年以上惩役;致人死亡的,处死刑或者无期惩役。”由于抢劫致死伤罪的法定刑通常比以抢劫罪与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伤害致死罪数罪并罚处罚还要重,因而,各国理论与实务都严格限制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范围。
在德国,并非只要是抢劫行为引起死亡结果,就成立抢劫致死罪,理论界从对象与行为两方面限制抢劫致死罪成立范围。具体而言:(1)抢劫致死罪的对象限于他人,不包括抢劫行为的参与者(即抢劫的共犯),抢劫行为导致同伙死亡的,不能认定为抢劫致死罪。但这里的“他人”,不限于抢劫行为的被害者。例如,抢劫犯向追赶的被害人开枪,流弹导致无关的第三人死亡的,也能成立抢劫致死罪。[3](2)抢劫致死罪中的死亡结果,必须是由抢劫行为(包括抢劫财物的未遂行为)所引起。[4]强取财物的行为引起死亡结果的,例如,强取被害人维持生命所必要的药丸,或者强夺被害人赖以抵御严寒的衣物而冻死被害人的,只是成立谋杀罪(刑法第211条)与过失致死罪(第222条)的问题,不成立抢劫致死罪。[5](3)并非所有由抢劫引起的死亡结果,都属于抢劫致死,而必须是由作为抢劫手段的强要行为,即暴力、胁迫行为直接引起的结果,但不必限于直接、故意的身体伤害行为所引起;[6]由于受到抢劫犯及其同伙的攻击而逃跑的被害人跌倒致死的,也成立抢劫致死罪;因受胁迫而引起的死亡结果,如被害人受到行为人胁迫后休克死亡,亦成立抢劫致死罪;但是,抢劫犯及其同伙的暴力、胁迫对被害人或者第三者的死亡没有直接影响的,不成立抢劫致死罪,例如,追赶抢劫犯的警察向抢劫犯开枪,流弹导致第三人死亡的,不成立抢劫致死罪。[7](4)抢劫致死罪,一般发生于抢劫着手至既遂期间;[8]事后抢劫中暴力、胁迫引起死亡结果的,也成立抢劫致死,而且由于事后抢劫的主体包括抢劫犯,因而抢劫既遂后,抢劫犯为了逃脱抓捕而向追踪者开枪,以及银行抢劫犯为了逃跑而与警察展开枪战,抢劫犯射出的流弹导致路人死亡的,也成立抢劫致死罪。[9]但是,抢劫犯搬运赃物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无关的行人死亡的,由于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没有特别的关联,仅成立抢劫罪与过失致死罪,数罪并罚。[10](5)只有行为人对具体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存在预见,才符合抢劫致死罪主观方面的轻率要件。例如,行为人虽然没有杀人的故意,但用棍棒猛敲被害人头部,致其头盖骨破裂而死的,成立抢劫致死罪。[11]但是,放任因抢劫行为受重伤的被害人不管致其死亡的,不能评价为轻率,不成立抢劫致死罪,而是构成不作为的谋杀罪。[12]
由于日本刑法规定的抢劫致死伤罪的法定刑极重,尤其是抢劫致死罪的起点刑就是无期徒刑,比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还要重,[13]因而,日本刑法理论与判例也严格限制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范围,主要有四种观点:(1)“手段说”认为,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限于由作为抢劫手段的暴行、胁迫而引起死伤结果的场合。[14]手段说的优势在于标准的明确性,不足在于,可能导致抢劫致死伤罪的处罚范围过于狭窄。例如,盗窃犯在逃跑中为抗拒抓捕、隐灭罪迹而使用暴力致人死伤,虽然不能说是作为抢劫手段(即不是作为强取财物的手段)的暴力、胁迫引起死伤结果,但根据刑法第238条事后抢劫罪的规定,还是应该认定为抢劫致死伤罪。又如,抢劫犯在抢劫既遂后的逃跑过程中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致人死伤,虽然也不能说是作为抢劫手段的暴行、胁迫引起死伤结果,但判例一般认为这种情况下成立抢劫致死伤罪。[15](2)判例采取的是“机会说”,认为只要是在“抢劫的机会”之下,发生了死伤结果即可。[16]机会说的实质性根据在于,将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直接限定于作为抢劫手段的暴力、胁迫以及类似情况下所实施的暴力、胁迫。[17]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机会说会导致抢劫致死伤罪的处罚范围过宽。例如,按照机会说,在抢劫过程中为了发泄对被害人的日常私怨,利用抢劫的机会将其杀害,或者在抢劫过程中碰巧遇到以前的仇人而乘机杀死仇人的,或者抢劫犯在抢劫过程中发生内讧而相互残杀的,以及抢劫犯在抢劫过程中不小心踩死了地上的婴儿等等,都因为发生于“抢劫的机会”中,而可能成立抢劫致死伤罪,从而不当扩大了其成立范围。[18](3)“密切关联性说”认为,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虽然不能仅限于由作为夺取财物之手段的暴行、胁迫而造成死伤结果的场合,而应包括由“抢劫的机会”下所实施的原因行为所造成的死伤结果;根据刑法第240条抢劫致死伤罪的立法宗旨,死伤结果应限于该原因行为在性质上通常是伴随抢劫所实施的,即和抢劫行为具有密切关联性的场合。这就是多数学者所主张的密切关联性说。[1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对机会说进行限定而主张密切关联性说并没有必要,况且密切关联性说的标准依然模糊。[20](4)扩张手段说认为,由作为抢劫手段的暴行、胁迫,或者与事后抢劫相类似状况下的暴行、胁迫,造成了死伤结果的,就应肯定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21]笔者认为,既然事后抢劫也以抢劫罪论处,则事后抢劫中的暴力、胁迫行为,当然属于作为抢劫手段的行为,这种行为导致他人死伤的,理当成立抢劫致死伤罪。故没有必要迁就事后抢劫,而将作为抢劫手段的暴力、胁迫行为进行扩张。至于抢劫犯在逃跑过程中为防止财物的夺还、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致人死伤的,当然属于与抢劫行为具有密切关联性的、抢劫犯罪中通常伴随的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因而,采取密切关联性说,可以使抢劫致死伤罪处罚范围适中。至于密切关联性说仍具有模糊性,会导致处罚与否界限不明确的问题,应该说,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精确,都少不了根据情况进行具体判断、斟酌。由此,笔者倾向于密切关联性说。
日本有一个判例:被告等人在位于大楼二楼的中式风俗店,持气枪胁迫店长B等人,抢走现金6万日元。当时,该店经营者A女正在其他房间休息,察觉到被告等人入室抢劫后,为了躲避危险,从窗口跳下而受伤。判决指出:“由于在抢劫的机会之下,伴有致人伤害等行为的情形不在少数。因此,作为抢劫罪的加重类型,规定了‘抢劫致人负伤的’,成立抢劫致伤罪。由此可见,要成立抢劫致死伤罪,仅仅是在抢劫现场发生了致人死伤的结果,还不能成立,必须是能评价为,伤害等结果的发生,是基于抢劫犯在抢劫时所通常实施的行为……比照受害店铺当时的情况,以及被告等人的行为样态,当时在店铺的人,即便没有被气枪顶住并受到胁迫的B等人的情况,要不被被告等人发现逃出店铺,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如果被被告等人发现,就会与B等人一样受到胁迫。他们这样考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被告人用气枪顶住B等人加以胁迫的行为,可以评价为,该胁迫的威力已客观上影响到当时在店铺内的所有人……抢劫当时,被告等人尽管对A在受害店铺之内这一点,并无具体的认识,但处于完全可认识到A之存在的状态之下,被告等人用气枪顶住B等人的行为,客观上可以评价为,对当时在店铺之内的A也实施了胁迫。因此,只要由此处于恐惧状态的A是试图从窗口跳到地上而受伤,认为被告等人应负抢劫致伤罪的罪责,就是妥当的。”[22]
韩国也有一个判例:接到被害人的抢劫报告后到达现场的警察乙和丙发现,在离现场150米的地方,抢劫犯人甲开着卡车逃跑。警察乙和丙好不容易抓住被告人,但由于甲的力气太大,乙和丙没法给他戴上手铐,只能把甲推入警察车辆。被告人趁此机会用水果刀杀死坐在旁边的警察乙。韩国大法院判决认为:“抢劫杀人,是指抢劫犯人,借抢劫之机杀死他人而成立的犯罪。因此,其杀人行为应当实施在从抢劫罪的实行着手到实行中或者实行之后不久,以及抛弃实行意图之后不久等社会普通观念上足以认定犯罪行为还未结束的期间里。”由此,“原审对上述公诉事实,以由于被告人的杀人行为和抢劫行为在时间上、距离上的靠近性,犯罪行为还处在社会普通观念上还未结束的状态下发生为理由,判决为抢劫杀人罪。该判决是正确的,并没有误解抢劫杀人罪的法理。”[23]
我国刑法通说教科书指出,“‘抢劫致人重伤、死亡’,是指行为人为劫取公私财物而使用暴力或其他强制方法,故意或过失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24]这相当于日本刑法理论中的“手段说”。但手段说会导致抢劫致死伤成立范围过窄。另有教科书指出,“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是指犯罪分子在抢劫公私财物过程中,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引起的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25]这种观点相当于日本刑法理论中的“机会说”。但机会说可能导致抢劫致死伤处罚范围过宽,也不具有合理性。
还有学者指出,认定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特别要求抢劫行为与重伤、死亡之间具备直接性要件,且行为人对重伤、死亡具有预见可能性。”例如,“为了抢劫捆绑被害人,逃走时忘了为被害人松绑,导致被害人停止血液循环或者饿死的,应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但是,对于抢劫行为引起被害人自杀的,追赶抢劫犯的被害人自己摔地身亡的,抢劫犯离开现场后被害人不小心从阳台摔下身亡的,都不能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26]另有学者提出,“死伤结果与抢劫行为之间应当有一定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死伤结果是由与抢劫相关联的行为所引起,但不能要求死伤结果必须由作为抢劫手段的暴力、胁迫行为所直接产生。”[27]这基本上是密切关联性说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基本上是合理的。
有人指出,被害人因行为人在抢劫过程中的威吓、殴打导致疾病发作而死亡的,应当认定实施抢劫的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缺乏预见可能性,不成立抢劫致人死亡。另外,“有学者认为:如果抢劫是发生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被害人因害怕而后退以致被车撞死,行为人对这样的结果应有预见的可能,应承担抢劫致人死亡的责任。事实上,此种情形下的威吓、追赶只是被害人被车撞死的一个必要条件,死亡结果只是在这一条件基础上,又结合了当时的交通状况以及驾车人的反应能力和是否遵守了交通规则等情形才发生的。就抢劫的行为人而言,对这些情形显然既无法预见,更无法控制。因此,对这种死亡结果,不应直接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28]笔者不赞成上述观点。即便被害人身患疾病,若不遭受行为人的威吓、殴打,也不会导致疾病发作,除非是特异体质,一般不能否认抢劫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应对死亡结果承担责任。此外,既然抢劫发生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就不难预见被害人因车祸死亡的结果;即便肇事司机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过失,也不能否认抢劫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客观归责。因此,抢劫行为人应对被害人死亡结果承担责任。
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判例认为,追赶抢夺犯人的警察发生车祸死亡的,抢夺犯人不成立抢劫致人死亡。[29]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追赶的警察发生车祸死亡,并不是社会一般观念上所认为的抢劫行为所通常伴随的情况,行为人缺乏预见可能性,不应对死亡结果承担责任。同样,若追赶的警察开枪致路人死亡,一般也不能让行为人对死亡结果负责。不过,倘若抢劫犯与警察发生枪战,警察在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导致路人死亡时,行为人有可能对路人的死亡结果负责。
总之,“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必须是与抢劫行为具有密切关联性的、按照社会的一般观念系抢劫过程中所通常伴随发生的死伤结果。
二、抢劫故意杀人的定性
各国刑法一般都规定有抢劫致死伤罪,而以故意杀人的方式抢劫的,是成立抢劫致死伤罪还是成立杀人罪,抑或成立想象竞合犯而从一重处罚,是各国刑法理论与实务面临的问题。综观各国刑法理论与实务,对于抢劫故意杀人的如何定罪处罚,完全取决于抢劫致死伤罪与杀人罪法定刑轻重的比较,从罪刑均衡立场进行判断。
例如,德国刑法第251抢劫致死罪的法定刑为终身自由刑或者不低于十年的自由刑,而第212条故意杀人罪规定的法定刑,为不低于五年的自由刑,在特别严重的情形,处终身自由刑;第211条谋杀罪的法定刑,为终身自由刑。可以看出,在德国,故意杀人罪与谋杀罪的法定刑并不低于抢劫致死罪,即便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罚,也有可能以故意杀人罪或者谋杀罪定罪处罚。因而,德国刑法理论通说与判例认为,抢劫故意杀人的,成立抢劫致死罪与故意杀人罪或者谋杀罪的想象竞合犯;出于杀人的故意抢劫的,如果死亡结果没有发生,也成立抢劫致死罪的未遂与故意杀人罪或者谋杀罪的未遂的想象竞合犯,因为抢劫杀人或者抢劫谋杀,是应当比抢劫致死罪处罚更重的犯罪。[30]
又如,日本刑法第240条抢劫致死罪规定,抢劫致人死亡的,处死刑或者无期惩役,而刑法第199条杀人罪规定,杀人的,处死刑、无期或者五年以上惩役。可见,日本刑法规定的抢劫致死罪比杀人罪的法定刑还要重,因为前者起点刑是无期惩役,后者起点刑仅为五年惩役。关于抢劫故意杀人的定性,日本刑法理论曾经存在成立抢劫罪与杀人罪的想象竞合犯[31],以及抢劫致死罪与杀人罪的想象竞合犯[32]两种主张。日本以前的判例曾经认为,属于杀人罪与抢劫致死罪的想象竞合犯,[33]但后来判例态度发生转变,认为抢劫故意杀人的,仅适用刑法第240条后段即抢劫致死罪定罪处罚。[34]现在刑法理论的通说也支持判例立场的转变,即抢劫故意杀人的,仅适用抢劫致死罪定罪处罚。[35]判例和学说立场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如果肯定成立杀人罪与抢劫致死罪的想象竞合犯,显然是对“死亡”结果进行了重复评价,而如果认为仅成立杀人罪与抢劫罪的想象竞合犯,那么,与仅对死亡结果存在过失的场合(以抢劫致死罪定罪处罚,最低判处无期惩役)相比,刑罚反而更轻(因为最低可能判处五年惩役),处刑有失均衡。这样,日本刑法第240条抢劫致死伤罪条文,其实包含了抢劫杀人罪(存在杀人故意)、抢劫致死罪(对死亡结果仅存在过失)、抢劫伤害罪(存在伤害的故意)、抢劫致伤罪(不存在伤害的故意)四个罪名。[36]
在我国,抢劫故意杀人的,是定抢劫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在理论上曾经有过探讨。[37]但自从《抢劫杀人批复》出台后,通说教科书亦步亦趋,也认为抢劫故意杀人的,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38]不过,还是有个别学者认识到,在抢劫故意杀人未遂的情况下,若以抢劫罪论处,则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能比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处罚还要轻(因为即便是未遂,也明显不属于情节较轻的杀人)。因而,按照现行刑法规定,为了避免出现轻纵故意杀人犯的弊端,对于抢劫故意杀人未遂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是必要的和适当的。[39]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抢劫罪中的暴力行为是否包括故意杀人行为,在理论上存在肯[40]否[41]两种观点。张明楷教授指出,抢劫致人死亡包括抢劫故意杀人的情形。因为,“(1)刑法第263条并没有明文将‘致人死亡’限定为过失;认为只能是过失与间接故意的观点,不符合犯罪构成原理。既然过失致人死亡的,属于抢劫致人死亡;故意致人死亡的,当然也属于抢劫致人死亡。(2)当场杀死他人取得财物的行为虽然同时触犯了故意杀人罪,但以抢劫罪论处(抢劫罪的主刑与故意杀人罪相同,但附加刑高于故意杀人罪),完全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不会轻纵抢劫犯。(3)将当场杀害他人取得财物的行为以抢劫罪论处,可以避免定罪的混乱;将当场杀害他人取得财物的认定为抢劫罪,与故意致人重伤后当场取走财物的认定为抢劫罪,也是协调一致的。”[42]
笔者认为,抢劫罪的手段行为能否包括故意杀人,与抢劫故意杀人的是定抢劫罪还是故意杀人罪,不是同一个问题,不应混为一谈。既然一般的暴力可以成为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就没有理由否认杀人这种最极端的暴力手段也能成为抢劫罪的手段行为。问题在于,以故意杀人的方式抢劫的,是认定为抢劫罪合理,还是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更有道理。笔者认为,抢劫故意杀人的,成立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想象竞合犯,一般情况下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尤其是在抢劫杀人未遂(即未发生死亡结果)的情形,应当以故意杀人罪未遂论处。
首先,虽然抢劫致人死亡法定刑的主刑最高刑与故意杀人罪一样,同为死刑,而且前者还有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附加刑,但不能因此认为抢劫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与故意杀人罪持平,甚至高于故意杀人罪。因为,刑法理论公认,即便刑种相同,刑种的排列顺序不同时法定刑轻重也有差别。故意杀人罪之所以是刑法分则中唯一以死刑为首选刑种的罪名,是因为故意杀人罪在刑法分则中被公认为违法性与有责性最重。事实上,在保留个别死刑罪名的国家,也是仅保留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得出,抢劫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并不轻于故意杀人罪的结论。尤其是出于杀人的故意进行抢劫,而未致人死亡时,若以抢劫罪定罪,又根据抢劫致人重伤、死亡无未遂的司法解释的立场,最终只能以抢劫罪的基本刑,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处罚。相反,若承认抢劫故意杀人的,成立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罚的结果是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则抢劫故意杀人未遂的,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未遂,显然比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因为,抢劫杀人未遂的,不会属于情节较轻的杀人,按照故意杀人罪未遂论处,完全可能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其次,刑法中可能包含故意杀人情形的罪名,当符合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时,应尽量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这样一方面可以对外保持我国政府的良好形象,因为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符合死刑配置的原理,能够为公众所容忍;相反,我们若以抢劫罪判处了大量的死刑,只会给外国人留下财产比生命珍贵、中国政府草菅人命的印象。另一方面,将死刑的适用控制在故意杀人罪框架内,符合逐渐删减死刑罪名直至最终废止死刑的国际潮流。
再次,抢劫故意杀人的,以杀人罪论处符合人们杀人偿命的报应观念。抢劫杀人犯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与老百姓头脑中抢劫罪不过是财产犯罪的观念相悖,判决难以让“不明真相”的民众信服。固然在国外,抢劫杀人的,也会以抢劫致死罪或者抢劫杀人罪定罪处罚,但毕竟从其罪名中不难明白,行为人是因为剥夺了他人生命而被判处死刑。而从我国“抢劫罪”罪名中,难以解读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资讯。或许,摆脱司法解释的羁绊,对抢劫杀人的,直接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罪或者抢劫杀人罪,也能“名实相符”,从而顺应人们的报应要求。
再其次,认为对抢劫杀人的定抢劫罪有利于定罪统一的观点,其实不足为信。因为,对于抢劫杀人的,都以故意杀人罪定罪,也是一种统一,而且是一种更合理的统一。
最后,对于抢劫故意杀人的以杀人罪定罪处罚,可以实现在抢劫罪条文中保留死刑,而实际上废止死刑的效果。我国死刑罪名据称有五六十个,这种规模在全世界都屈指可数。但这不仅不应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地方,相反应是我们感到羞耻的地方。虽然目前国人尚难接受大规模废除死刑,但逐渐将死刑适用控制在故意杀人罪和贪污受贿罪,变相废除其他罪名的死刑,是完全应该、也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对抢劫故意杀人的定故意杀人罪,符合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能够推动我们加快废除死刑改革的步伐。
三、既未遂的认定
按照《两抢解释》的说法,抢劫致人重伤、死亡没有未遂的问题,但这种观点显然有违未遂犯原理。因为,一是抢劫致人重伤、死亡不过是抢劫罪的一种情形,而抢劫罪作为故意的财产犯,当未劫取到财物时,当然属于财产性质犯罪的未遂;二是理论通说认为,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包括抢劫杀人与抢劫伤人的情形,而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在未发生死伤结果时,当然属于人身性质犯罪的未遂。司法解释的错误在于,将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未遂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处罚混为一谈。是否存在未遂,与之后如何处刑,是相关却又不同的问题。其他国家刑法理论与实务的作法,也说明了这一点。
德国刑法理论仍将抢劫致死罪作为抢劫罪的一种,因而只有抢劫部分与致死部分均完成时,方成立抢劫致死罪的既遂。这样,德国抢劫致死罪的未遂就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未夺取到财物,但死亡结果发生的场合(即取财未遂型);二是意图以杀人的方式取财,但死亡结果未发生的情形(即杀人未遂型)。[43]对于取财未遂型,因为作为基本犯的抢劫罪未遂,故也成立抢劫致死罪的未遂,只是由于发生了死亡结果而成立伤害致死罪,所以属于抢劫致死罪的未遂与伤害致死罪的想象竞合犯。[44]此外,假如行为人本意只是拿枪胁迫被害人,由于失误导致被害人死亡,行为人震惊之余而放弃了夺取财物的,还能成立抢劫致死罪未遂的中止犯,抢劫部分不受处罚,仅就死亡结果成立伤害致死罪。[45]就杀人未遂型而言,德国刑法理论认为,不管夺取财物完成与否,均成立抢劫致死罪的未遂,与谋杀罪的未遂形成想象竞合犯。[46]
日本通说与判例重视抢劫致死伤罪对生命、身体安全的保护,因而只要发生了致人死伤的结果,不问是否取得财物,均成立抢劫致死伤罪的既遂;甚至于杀害被害人后放弃夺取财物而逃走的,也不妨碍本罪既遂的成立。[47]这与德国即便发生死亡结果,只要未取得财物仍成立抢劫致死罪未遂的观点不同。此外,由于日本通说认为,伤害的未遂仅成立暴行罪,而暴行为抢劫罪的手段所包含,因而,出于伤害的故意进行抢劫而伤害结果未发生时,仅成立抢劫罪。最终结论是,抢劫致死伤罪的未遂仅限于杀人未遂的场合。[48]不过,有力学说认为,抢劫致死伤罪的未遂,并不限于杀人未遂的场合,抢劫未遂时也构成抢劫杀人罪的未遂。[49]对此,通说批评指出,若是因为考虑到本罪是一种财产犯,在杀人达到既遂,仅仅因为抢劫未遂就认定为抢劫致死未遂罪,对于杀人已经达到既遂这一点,未免过于忽视。因此,还是通说、判例的立场更为妥当。[50]
在我国,关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既未遂,除司法解释所持的无未遂的立场外,还有几种观点:(1)“在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由于犯罪主要客体是财产法益,所以仍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51]这可谓取财标准说。(2)主张以出现重伤、死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的既遂标准。[52]这可谓死伤结果发生说,与日本的通说立场相似。(3)张明楷教授认为,一方面,“行为人原本打算故意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后强取财物,并已着手实行重伤、杀害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致人重伤、死亡的,即使强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也应适用加重法定刑,并适用总则关于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另一方面,“行为人致人重伤、死亡后未能强取财物的,严格地说,属于基本犯未遂,结果加重犯既遂。剩下的问题只是是否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未遂犯的处罚规定的问题。本文的看法是,由于我国的法定刑较重,法官量刑也偏重,故倾向于适用未遂犯的规定。”[53]
笔者认为,理论上之所以“纠结”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有无未遂,原因无他,即“把对结果加重犯的抢劫罪应当如何处罚与结果加重犯的抢劫罪有无既遂、未遂的状态混为一谈”[54]。抢劫罪侵害的是财产权与人身权双重法益,作为故意的财产犯罪,未取得财物当然是财产犯罪的未遂(基本犯的未遂犯);另一方面,作为故意的人身犯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发生死亡、伤害结果时,就结果加重犯而言,当然成立未遂犯(加重结果的未遂)。正如德国通说与判例的立场,只有同时取得财物与发生加重结果,才算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既遂;二者缺一的,仅成立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未遂。日本通说之所以认为,抢劫致死伤未遂取决于死伤结果发生与否,而与取财完成与否无关,原因可能在于,抢劫致死伤罪的法定刑比伤害罪、杀人罪还要高;显然,关于抢劫致死伤罪立法的价值取向偏重对人身权的保护,如果发生了死伤的结果,还认为成立未遂,不仅在观念上难以接受,而且与普通伤害罪、杀人罪的既遂也不相协调。而德国,之所以承认在取财未遂而致死既遂时,仍成立抢劫致死罪未遂,是因为其理论通说认为,抢劫故意杀人的,成立抢劫致死罪与故意杀人罪或者谋杀罪的想象竞合犯,在出于伤害的故意而导致死亡结果时,即便因为取财未遂而成立抢劫致死罪的未遂,同时也能与伤害致死罪之间形成想象竞合犯。而日本,由于抢劫致死伤罪法定刑高于伤害罪、杀人罪法定刑,理论通说与判例均认为,抢劫杀人的,仅成立抢劫致死罪,否认抢劫致死罪与杀人罪之间想象竞合犯的成立,而伤害未遂仅成立暴行罪,最终导致抢劫致死罪未遂仅限于杀人未遂的情形。
我国刑法关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法定刑,并不高于故意杀人罪,也不高于故意伤害罪(因伤害致死及残忍伤害的,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与入户抢劫等其他七种纯粹财产性质的加重犯,适用同样幅度的法定刑,也说明我国刑法中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并非偏重人身权的保护。由此,我们认为,可像德国一样,承认抢劫杀人、伤人的,成立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之间的想象竞合犯。尤其是在抢劫杀人而未发生死亡结果时,成立抢劫致人死亡的未遂与故意杀人罪的未遂,以及抢劫伤人而发生死亡结果时,成立抢劫罪的既遂或者未遂(未取得财物)与故意伤害致死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罚。如此,便不会出现罪刑不相适应的局面。而且,我国未遂犯处罚规定采取的是得减而非必减的立场,即便认定为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未遂犯而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也不会轻纵罪犯。
总而言之,我们之所以承认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存在基本犯未遂与加重犯未遂两种未遂犯情形,一方面是为了遵循故意犯的既未遂原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司法更精细化,将基本犯与加重犯均既遂的情形,与基本犯或者加重犯未遂的情形相比较,在量刑上尽量区别对待。
四、共犯的认定
德国刑法规定成立抢劫致死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至少抱着轻率的心态,在数人共同实施抢劫行为时,其中一人的行为直接引起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其他共犯人对于死亡结果,在主观上也必须至少具有轻率的态度。[55]换言之,只要对于死亡结果至少存在轻率的主观心态,其中一人引起的死亡结果,其他共犯人也应承担抢劫致死罪的刑事责任。[56]而且,不管直接引起死亡结果的人自身对于死亡结果是否出于轻率的态度,对于其他共犯人刑责的承担不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便被教唆者对于死亡结果连过失都没有,只要教唆者对被教唆者所引起的死亡结果存在轻率的态度,教唆者自身也应因自己的轻率而承担抢劫致死罪的刑事责任。[57]
日本判例认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与加重的结果之间只要具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即可,不要求行为人存在过失。[58]从这种立场出发有一个判例:A和B共谋实施抢劫,抢劫过程中因被害人大声叫嚷,引来警察抓捕,二人仓皇逃窜。B为了避免逮捕而攻击警察,导致警察死亡。判决认为,B的伤害致死行为发生在抢劫的机会中,抢劫共谋者A应当对其他共犯人在抢劫机会中造成的死伤结果负责。因而,A也应承担抢劫致死加重结果的责任。[59]关于结果加重犯,通说不同于判例的立场,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据此,行为人故意实施蕴含发生加重结果危险性的犯罪行为的,没有理由不将加重结果归责于他。故而在实际结论上,日本通说与判例立场之间没有大的差异。[60]
笔者认为,密切关联性说同样适用于抢劫共同犯罪的认定。部分共犯人在与抢劫行为具有关联性的场合,若其中一人逃跑中为抗拒抓捕致他人死亡,只要其他共犯人对死伤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就应当承担责任。而对于作为暴力性犯罪的抢劫罪而言,其行为本身就蕴含着致人死伤的高度危险性,因而否定行为人对死伤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往往是很困难的,由此,抢劫共犯中一人引起被害人死伤结果的,其他共犯人通常都应承担抢劫致死伤的责任。
不过,根据因果共犯论,行为人仅对与自己的行为具有物理或者心理因果性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61]而且,原因只能出现在结果之前。因而,共犯人只能对其参与之后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这是我们在处理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应当注意的。
例如,甲正在对丙实施暴力进行抢劫,恰逢甲的朋友乙路过,甲与乙经过意思沟通,共同对丙实施暴力,最终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但因为不能查明死伤结果是否发生在乙参与暴力之后,即不能排除关键性致死伤的行为发生在乙参与之前的可能性,乙与甲虽然成立抢劫罪共犯,但只能由甲单独对被害人死伤结果负责,即甲单独成立抢劫致人重伤、死亡。
又如,王某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进行抢劫,已经压制住被害人的反抗,这时王某的朋友张某参与进来共同取走被害人的财物。后经鉴定,被害人身受重伤。由于张某在参与进来之前,王某已经抑制住被害人的反抗,重伤结果也是发生在抑制被害人反抗过程中,张某仅仅参与了取财行为,不仅与被害人受重伤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而且与被害人遭受暴力而被压制反抗也没有因果关系。这与参与前被害人已经死亡或者昏迷,或者已被捆绑的情况没有不同。由于张某只与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因而张某仅在盗窃罪范围内与王某成立共犯,王某单独承担抢劫致人重伤的刑事责任。
日本曾有一个经典判例:丈夫X告知妻子Y自己已经出于抢劫的目的杀害了被害人,并要求Y帮助寻找财物。妻子Y迫不得已答应了丈夫的要求,手举蜡烛帮助丈夫顺利找到了被害人的财物并取走。判例认为,由于抢劫杀人罪是单纯一罪,在加担、帮助属于该抢劫杀人罪的部分行为的夺取财物行为时,成立抢劫杀人罪的帮助犯,而不只是成立单纯的抢劫罪或者盗窃罪的帮助犯。[62]对该判例,虽然学界持肯定立场的不在少数,但仍遭到有力学者的批判。例如,日本平野龙一教授指出,因为认识到了丈夫的杀人事实这一人格态度,就认为是抢劫杀人罪的共犯,与之前单独实施了杀人行为的丈夫承担相同的刑责,这不过是要求共犯的罪名必须同一的完全犯罪共同说的立场的体现罢了。不管有什么样的人格态度值得非难,都不应让行为人对与自己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和结果负责。[63]日本大谷实教授也批判指出,妻子没有与丈夫共同引起杀人的结果,即妻子中途参与后的行为与杀人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故应当否定抢劫杀人罪的承继共犯的成立,只是成立抢劫罪的帮助犯。[64]
对于上述日本判例,笔者认为,既然妻子在参与取财之前,丈夫已经杀死被害人,妻子的参与行为不仅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不成立抢劫致人死亡的共犯,而且由于没有参与实施暴力行为,因而与被害人遭受暴力致使反抗被压制的结果也没有因果关系,其只是利用了被害人丧失控制财物的能力的事实,所以妻子的行为仅与被害人丧失财物占有的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若是发生在荒郊野外,妻子的行为仅承担侵占罪(侵占脱离占有物)的刑事责任,若是发生在某个空间内而且存在其他的空间管理人,则承担盗窃罪的责任。总之,利用被害人已死的事实参与取财的,既不能成立抢劫致人死亡的共犯,也不成立抢劫罪的共犯,只应承担侵占罪或者盗窃罪共犯的责任。
【作者简介】
陈洪兵(1970-),男,湖北荆门人,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日本首都大学东京客员准教授,从事刑法解释学研究。
【注释】
本文为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研究”的成果之一。
[1] 参见张明楷:“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第7、15页。
[2] 杨兴培:“抢劫罪既遂、未遂的司法解释质疑——兼论司法解释的现实得失与应然走向”,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6期,第133-134页。
[3] Vgl. Herbert Tr?ndle/ Thomas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 51.Aufl. (2003), §251 RdN. 3; Adolf Sch?nke/Horst Schr?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7., neu bearbeitete Aufl. (2006), §251 RdN. 3 (Eser).
[4] Vgl. Kindh?user, BT Ⅱ., §15 RdN. 3.
[5] Vgl. Adolf Sch?nke/Horst Schr?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7., neu bearbeitete Aufl. (2006), §251 RdN. 4 (Eser).
[6] Vgl. Kindh?user, BT Ⅱ., §15 RdN. 3; Harro Otto, Grundkurs Strafrecht, Die einzelnen Delikte, 6., neubearbeitete Aufl. (2002), §46 RdN. 40.
[7] Vgl. Adolf Sch?nke/Horst Schr?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7., neu bearbeitete Aufl. (2006), §251 RdN. 5 (Eser).
[8] Vgl. Kindh?user, BT Ⅱ., §15 RdN. 5.
[9] BGH 38, 298; BGH NJW 1999, 1039; Strafgesetzbuch, Leipziger Kommentar, 11 Aufl, §251 RdN. 6(Herdegen).
[10] Vgl. Harro Otto, Grundkurs Strafrecht, Die einzelnen Delikte, 6., neubearbeitete Aufl. (2002), §46 RdN. 42; Adolf Sch?nke/Horst Schr?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7., neu bearbeitete Aufl. (2006), §251 RdN. 4 (Eser).
[11] Vgl. Harro Otto, Grundkurs Strafrecht, Die einzelnen Delikte, 6., neubearbeitete Aufl. (2002), §46 RdN. 42.
[12] Vgl. Adolf Sch?nke/Horst Schr?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7., neu bearbeitete Aufl. (2006), §251 RdN. 6 (Eser).
[13] 日本刑法第199条杀人罪规定:“杀人的,处死刑、无期或者五年以上惩役。”
[14] 参见[日]泷川幸辰:《增补刑法各论》,世界思想社1951年版,第131页。
[15] 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六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186页。
[16] 参见日本大判昭和6年10月29日刑集10卷511页;最判昭和24年5月28日刑集3卷6号873页。
[17] 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六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186页。
[18] 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3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240页;[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有斐阁2010年版,第235-236页。
[19] 参见[日]佐久间修:《刑法各论》(第2版),成文堂2012年版,第209页;[日]松宫孝明:《刑法各论讲义》(第3版),成文堂2012年版,第233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3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240页。
[20] 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有斐阁2010年版,第236页;[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六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186页。
[21] 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有斐阁2010年版,第236页;[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六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186页。
[22] 参见日本东京地判平成15年3月6日判タ1152号296页。
[23] 参见[韩]吴昌植编译:《韩国侵犯财产罪判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24]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4页。
[25] 王作富主编:《刑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26] 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63页。
[27] 周光权:《刑法各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28] 参见李萍:“‘抢劫致人死亡’疑难问题探讨”,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7期,第51页。
[29]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5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刑一终字第13号刑事裁定书。
[30] Vgl. RG 63 105; BGH 9 135; Adolf Sch?nke/Horst Schr?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7., neu bearbeitete Aufl. (2006), §251 RdN. 9 (Eser); Harro Otto, Grundkurs Strafrecht, Die einzelnen Delikte, 6., neubearbeitete Aufl. (2002), §46 RdN. 48; Herbert Tr?ndle/ Thomas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 51.Aufl. (2003), §251 RdN. 6; Jecoks, Strafgesetzbuch Studienkommentar, 3. Aufl. (2001), §251 RdN. 13.
[31] 参见[日]泷川春雄=竹内正:《刑法各论讲义》,有斐阁1965年版,第183页。
[32] 参见[日]小野清一郎:《新订刑法讲义各论》(第3版),有斐阁1950年版,第244页;[日]泷川幸辰:《增补刑法各论》,世界思想社1951年版,第132页。
[33] 参见日本大判明治43年10月27日刑录16辑1764页。
[34] 参见日本大连判大正11年12月22日刑集1卷815页;最判昭和32年8月1日刑集11卷8号2065页。
[35] 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论讲义》(第5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313页;[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六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185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3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239页。
[36] 参见[日]伊藤真:《刑法各论》(第4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172页;[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有斐阁2010年版,第237页。
[37] 参见刘明祥:“论抢劫罪的加重犯”,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50页。
[38]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4页;周光权:《刑法各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39] 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四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1032页。
[40] 参见李萍:“‘抢劫致人死亡’疑难问题探讨”,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7期,第50-51页。
[41] 参见王晓民:“抢劫罪中暴力行为不宜包括故意杀人”,载《检察日报》2008年2月4日,第3版。
[42]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63页。
[43] Vgl. Adolf Sch?nke/Horst Schr?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7., neu bearbeitete Aufl. (2006), §251 RdN. 7 (Eser); Jecoks, Strafgesetzbuch Studienkommentar, 3. Aufl. (2001), §249 RdN. 13.
[44] Vgl. Herbert Tr?ndle/ Thomas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 51.Aufl. (2003), §251 RdN. 6.
[45] Vgl. Jecoks, Strafgesetzbuch Studienkommentar, 3. Aufl. (2001), §251 RdN. 14.
[46] Vgl. Herbert Tr?ndle/ Thomas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 51.Aufl. (2003), §251 RdN. 6; Jecoks, Strafgesetzbuch Studienkommentar, 3. Aufl. (2001), §251 RdN. 13.
[47] 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3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241页。
[48] 参见[日]浅田和茂、井田良编:《刑法》,日本评论社2012年版,第540页。
[49] 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11页;[日]中山研一:《刑法各论》,成文堂1984年版,259页;[日]曾根威彦:《刑法各论》(第5版),弘文堂2012年版,140页。
[50] 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六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187页;[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论讲义》(第5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315页。
[51] 沈志民:“抢劫罪既遂与未遂区分标准新探”,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第77页。
[52] 参见张苏:“论‘抢劫致人重伤、死亡’认定中的几个问题”,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38页。
[53] 参见张明楷:“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第15页。
[54] 参见杨兴培:“抢劫罪既遂、未遂的司法解释质疑——兼论司法解释的现实得失与应然走向”,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6期,第132页。
[55] Vgl. Herbert Tr?ndle/ Thomas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 51.Aufl. (2003), §251 RdN. 5.
[56] Vgl. Adolf Sch?nke/Horst Schr?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7., neu bearbeitete Aufl. (2006), §251 RdN. 8 (Eser).
[57] Vgl. Herbert Tr?ndle/ Thomas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 51.Aufl. (2003), §251 RdN. 5; Adolf Sch?nke/Horst Schr?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7., neu bearbeitete Aufl. (2006), §251 RdN. 8 (Eser)..
[58] 参见日本最判昭和26年9月20日刑集5卷10号1937页;最决昭和32年3月14日刑集11卷3号1075页。
[59] 参见日本最判昭和26年3月27日刑集5卷4号686页。
[60] 参见[日]神元隆贤:“强盗关连罪の身分犯的构成(一)”,载《成城法学》75号(2007年),第152页。
[61] 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4版),成文堂2012年版,第399页。
[62] 参见日本大判昭和13年11月18日刑集17卷839页。
[63] 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Ⅱ》,有斐阁1975年版,第382页。
[64] 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4版),成文堂2012年版,第445页。
